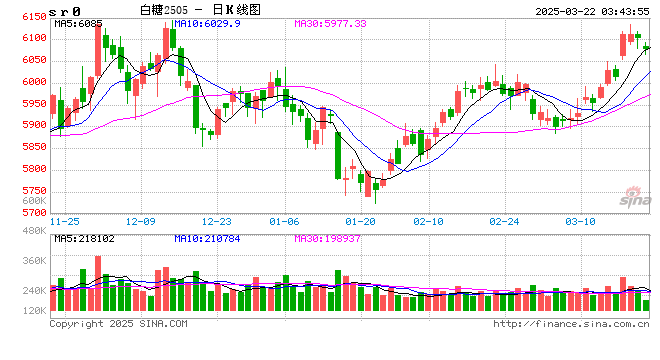 热点栏目
热点栏目原标题:“亚洲糖王”郭鹤年的期货往事 | 解读糖王的交易 经营 管理 操盘 人性
来源:云南糖网
1、小试牛刀
 郭鹤年
郭鹤年从1960年起,我每年去伦敦一两趟,有时从伦敦再飞纽约。
如果我要经营糖厂,就需要知道如何管理原糖成本,于是我开始摸索和学习做期糖生意。
因为没有人从旁教导,所以我去伦敦时,便不断观察英国人如何做交易,并不时询问一些有关运作机制的问题。
为了试水,我有时会做5或10批货的单(每批货为5公吨)。若亏蚀了也不会招致大损失;若赚了,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学习,并从中去开始感应市场的脉搏。
1963年我开始疯狂地做起交易来。这一年,我一共去了伦教四次,春夏秋冬各一次。每一次,我都留在入住的酒店简单地进行交易而且还赚了不少钱。
春天那次,获利丰厚;夏天则相对少些;秋天那次,经历了四周恶战后暴赚了一笔;冬天的盈利则与春天的差不多。
但在最后结数时,有几个交易商纷纷来向我哭诉出于同情,我让出了部分收益给他们。
一年下来,我的现金纯利相当于1,400万马币(接近500万美元),这是一笔巨款。之前郭氏兄弟的全部资金最多也不过约500万马/坡币。
市场经历了数年停滞,糖价一直徘徊于每吨2到28英镑之间。一直至1963年,市场开始复苏,但情况却不是一面倒地向上。
那年夏天,我不断入货,而走势也一直向好这对我极为有利。我很快便赚到了5万英镑,然后是10万英镑。夏末时,我对市况更为乐观,于是便通知新加坡的经纪:“买,买,买!”。
我在新加坡不断入货,持有实货约2万吨。我还不断买入期货,合计每吨均价为35英镑,而市价约为40英镑。
但后来价格突然崩溃狂泻至33英镑,而且看来还要再跌。若价格持续下挫,我将会一败涂地。
那时候,伦敦的所有交易商均被打得措手不及,大家都紧绷着脸,笑不出来。
又过了10到12天胆战心惊的日子,当时市价一度跌至约30英镑,然后开始横向整固。
直至9月,飓风弗洛拉开始横扫加勒比海。这场有史以来最致命的风暴侵袭当时全球最大的糖出口国古巴,严重损坏甘蔗田。
一时间,电话响个不停,电报横飞,糖价马上飙升。接下来的十多个交易日,糖价一路暴涨至每吨60多英镑。
当然,价格上涨到48、49、50英镑时,我已全数出货获利了这个秋季之旅,是我人生中以最短时间赚得最多的一次。
2、福祸相依
12月的首两星期,又因为一场飓风即将侵袭古巴,我在伦敦又赚了不少钱。
一个周五,所有交易平仓后,便预订了第二天中午回新加坡的机票。
当日下午四点钟,我突然接到来自德雷克公司一位资深交易员来电。他说:“罗伯特,我遇到麻烦了。不知道你能否出手相助?”
我问:“什么事?”
他说:“我为一个客户下了单,但现在他却食言了。我只是个员工,只能自掏腰包填补。你能否帮我接了这张单?”
他们很会编故事来博取同情,但本着郭氏家族宽宏大量之心,我同意接手帮他。
另外一次发生于周六清晨。我正要动身往机场,另一经纪致电求救。
我一般不喜欢在离开伦敦前尚有未平仓的交易,但华人般都较为感性,而且由于整年都做得不错,于是我便答应了。
我本应马上结算了事,这样损失不大。但是,我却固执地继续持有最后招致两三倍的损失。这两笔交易让我亏损了大约15万英镑。
为了帮两个朋友,我损失了12月份所赚的一大部分利润。
3、随机应变
我在1963年食糖交易上的成功,首要归功于我对英语及其文化的掌握。
在我开始经营那一刻开始,我就像一条变色龙似的随着环境来改变自己,适应不同的状况。
我在英国殖民地长大,受英国老师的教导。父亲于战后获得军方合同后,我便认识许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官,后来还成为友好。因此在英国时,除了我皮肤眼晴和头发的颜色外,我很容易便能融入当地社会。
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移民,但他却深受马来人和柔佛官员的欢迎。我遗传了父亲的公关技巧,这让我在英国人的社会更加如鱼得水。
良好的社交技巧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,但它必须发自内心的美善。
我在英国交朋结友,正如戴尔·卡耐基( Dale Carnegie)所说,我能影响他人。
我与市内所有主要食糖经纪交朋友、喝酒、吃饭,花钱如流水。只有中国人才懂得这种行之有效的公关技巧——自己省吃俭用,却对朋友慷慨大方。
要成为成功商人,你每天都得像刷牙一样,擦拭所有感官。我称之为“磨砺商业感官”,这包括视觉丶听觉、嗅觉、触觉和味觉。每一种感官都有其用武之地。
每当我走进一间房子,可以在眨眼间便能看清一切。如果屋子里有超过20个人,我可能需要多点时间来审视各人。但如果屋里只有6个人,我一进门便能马上知道发生的一切,我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气氛是紧张还是和谐。
期货交易的成功取决于你对市场的触觉,这是一种直觉和节奏。
我会与不同经纪交谈。每间公司都有一些年轻精明的英籍交易员,其中偶有一两个狡猾的,但总体来说,英国人还是较为率直。每个人都有身处顺风和逆境之时。因此,我会跟所有人都聊一下,以便了解更多。
我惯常会到德雷克公司逗留约20分钟,说句再见后,又转去戈洛杰茨( Golodetz),紧接到曼氏公司,然后再多去一两家。
我心想:“今天是基斯·塔尔博特( Keith Tal-bo),还是罗伊,泰勒( Roy Taylor)的幸运日呢!我会问选中的交易员一两个问题,如‘你今天准备怎样交易?’”
如果罗伊·泰勒说:“我会买进。”
我就跟风买进,这种方法四次有三次都奏效。我会在当日选取我认为有良好直觉和最佳判断力的人,然后支持他。
我从不看,也不相信图表,图表对我来说就像解剖学报告只是事后孔明。
没有图表能预测未来,这只不过是交易员用来引诱更多炮灰投入交易市场的众多武器之一。一切统计资料尽在脑中,并且不断更新。
当台风弗洛拉袭击古巴时,我运用智慧去推测市场反应。
你不能在大家买入时跟着买,也不能待大家都抛售时才出货。你必须比别人走快两三步,快一步都还不够。
我也得益于英国的阶级制度:英籍交易员彼此间从不作沟通。
他们都是资深交易员’是糖业终端协会( Sugar Terminal Association))的正式会员,而我只不过是个准会员。这五六家公司的顶级交易员能掌握市场上最新丶最快的资讯,而我只能滞后两个小时才得到。如果他们之间能有充分沟通,我就玩完了。幸好他们鲜有交流。
如果某人毕业于牛津某院系,而另一人来自牛津较次级的院系,或者来自剑桥或诺丁汉,那这他们之间便会互不理睬了。但由于我不从属任何体系,反而能跟他们所有人交流。
有一次我去戈洛杰茨公司,听到他们说无法卖出波兰的一批糖。我马上乘电梯下楼,赶到马路对面的德雷克公司,把糖卖给了他们,一吨赚了一英镑。结果皆大欢喜。
只要做到谦虚、正直不欺诈、不乘人之危,这世界上就有做不完的生意。
我即使掌握了很多市场资讯,也从不胡来。我是一个坚信原则的商人,所以大家都挺喜欢我。若错算了利润,我们会马上退回,从不争辩。
1963年,伦敦也有其他亚洲地区来的商人,但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像我这么勤奋。
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都汇集于伦敦,但他们的交易员就如机轮上的小齿轮,就连他们在伦敦或东京总部的管理层也看轻他们。
日本无疑是个贸易大国,但大公司里的职员却不精通商品交易。他们把生意都交给有关联的日本公司,或带他们外出享用美酒佳肴的人,这就是他们的交易方式。
“在商品交易中,亏损的痛楚让人痛入心腑。相反,大额盈利所带来的狂喜就如香槟上头般兴奋。所以交易者必须投入自己的资金才会用心。”
而日本资金的拥有者是银行,由一个极大的官僚架构来操控。当然,这是一个笼统的看法。
我相信日本也有优秀的交易商,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。
4、生逢其时
回到1960和1970年代,海洋里都处是鱼儿,鲨鱼偶有两条。对我而言,在这样的水域里捕鱼简直是轻而易举。
至今,尽管市场变化不大,但鲨鱼却多了很多。有时,海里小鱼好像已所余无几,有的只是鲨鱼。
这一行雇用了大批理科、工科的荣誉毕业生,也有博士生不断努力地优化规则系统,我对这些全然不懂。
如果1960和1970年代有今天的科技和资讯传播速度,我肯定自己就像一条离水之鱼,难以生存。
我的成功并不是依靠科技。
今天,依然有人赚钱、有人亏钱,但竞技场的地面已变得越来越湿滑。
人真的要生逢其时。
1963年,我去了英国四次,做食糖交易。1964年又去了两三次,之后每年我都会去英国。
凭着我们的努力和一点精明,公司在1958至1999年期间在糖业上获得了丰厚利润。唯一一次濒临灾难边缘的就是1963年9月,幸得飓风弗洛拉来拯救了我。
我记得1964年12月的一天,伦敦某晚报称我为“东方糖王”。这个称号就是从那时起流传开去。
称谓的来源,是由于我是全球少数几个完全整合了糖业生产和贸易的工业家之一,我们的业务覆盖了糖业的所有范畴。纵使如此,我总觉得“糖王”这个称谓还是不太恰当。
5、节奏交易
每次离开伦敦飞回新加坡时,总有远离壁炉800英里之感。
因为在伦敦时,就仿如坐在烧得熊熊的炉火前,对要添加多少柴火了如指掌。若只远观遥距作业,我根本无办法超越任何人。
我发现,只有一种方法能进行遥距贸易,就是“节奏交易”——这是我自创的一个词。
在学跳探戈或桑巴舞时,你就会知道跳得好全靠节奏。老师会告诉你,现在左脚往后、往后、往前侧步。可一旦节奏出错,你就必须专注去听音乐,再重新找回平衡。
千万不要让任何人,包括坐在身边的至爱对你说:“罗伯特,伸出右脚。”
旁观者越介入,你就越糊涂。所以,即使你时间掌握不好出了错,只要注意节奏,你是会重新跟上的。
在交易中,如果我感觉节奏出了偏差,我就会减少交易量,以降低风险。
在我的商业生涯中,节奏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。
整体上,英国的糖交易商都是最聪敏和精明的。
我遇到的第一个糖交易商是罗伊·费希尔( Roy Fisher),他于1959年来到马来西亚。我记得曾带他去光顾吉隆坡一家叫金鸡酒店(LeCqdOr)的仿法国菜餐厅,我们后来还成为了密友。
罗伊在J·V·Drake ltd工作,该公司不久便与一家咖啡、可可豆贸易公司合并,改名德雷克公司。J·V·Drake Ltd 的董事长是汤姆·德雷克上校( Colonel Tom drake),是弗朗西斯·德雷克爵士( Sir fran-cis Drake))的直系后裔。罗伊·费希尔是该公司白糖部的第二号人物,他的顶头上司是艾伦·亚瑟( Allan arthur),是一位前英国殖民政府公务员,其妻子唐(Dawn)是德雷克家族的成员。
另一位很卓越的交易商,是来自曼氏公司的迈克尔·斯通(Michael Stone),我们也成为了很亲密的朋友。该公司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行内的老牌经纪公司。
我和迈克尔·斯通1961年首次碰面,他像从天而降似的来到新加坡见我。罗伊和迈克尔是那个年代两位最杰出的食糖交易商。
6、五五分账
大约在1958年间,我聘用了叶绍义( Piet Yap)。他当时为一间荷兰驻新加坡贸易公司 nternazio(前身为鹿特丹贸易公司)做食糖交易。
绍义是苏门答腊籍华人,会讲荷兰语、印尼语和英语。
有一天,跟他通电话说:“绍义,你何不离开这荷兰殖民主义公司呢?你知道荷兰已是夕阳西沉,而苏加诺( Sukarno)将会把荷兰人赶出印尼。不如来加盟我们吧!我们是一家年轻公司,正需要你。”
绍义生于印尼,他能争取印尼的生意,而他与苏达索( Sudarso)也有交情。苏达索是爪哇贵族,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(印尼国家后勤局成立之前的机构)的董事。
当时印尼很穷,急需外汇,于是政府规定食糖必须由本地农作物如椰子和西米来加工生产。在1960年初,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可以出口一点以离心机分解出来的食糖。
苏达索有时也会给予我们一些生意。我们与印尼的最初几笔交易是与J·V·Drake联手做成的。
我清楚记得第一笔交易的经过,那是1962年的一个公众假日。
我和绍义在办公室工作,他告诉我:
“我刚和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的 Bapak(意指父亲,是印尼的尊称)苏达索通电话。他以固定价格给我留了三万吨糖,为期一周。我现在给J·V· Drake发个电报,看看能否把糖卖给他们。你觉得我们一吨赚5先令怎么样?”
绍义这时已经坐在电报机前,并把J·V·Drake的艾伦·亚瑟( Alan Arthur)召唤到伦敦那端的电报机前。
绍义正要以电报发出报价时,我打断他说:“绍义、绍义,等等,等等!”
我想了一下,指示他写道:“我们手握印尼国家糖业委员会的三万吨糖(我并没有透露价格)。你们是否愿意与我们联手买卖,利润五五分账?若愿意我们将把整笔交易情况告知。”
艾伦·亚瑟回道:“非常乐意。”
我们与J·V· Drake联手做了几笔交易(我们之间并没有书面协议,靠的是合作伙伴关系)。当时,J·V·Drake已是国际知名的交易商,而我们才在摸索学习。
通过联手而非单做代理,我们成为了交易的主角。
我们承接了生意,由他们卖出,然后摊分利润。
一个是在东南亚冒起的新加坡华人公司,另一个是伦敦市首屈一指的食糖交易商通过这合作模式,彼此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。
这次联手交易是从印尼出口至欧洲、中东或日本。我们接货,而J·V·Drake则负责推销,相互之间不收取任何费用,所以双方均获得不错的盈利。
如果我们只是做代理商,纯粹把接到的生意转手,那每吨就只能赚取5先令佣金,也就是说,一笔一万吨的交易,我们只能赚2500英镑。
但联手后,假设我们以20英镑一吨的价格买入,24英镑卖出,我们两家就可以平分5万英镑。
版权及免责声明: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,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“融道中国”,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。凡转载文章,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。
延伸阅读
版权所有:融道中国